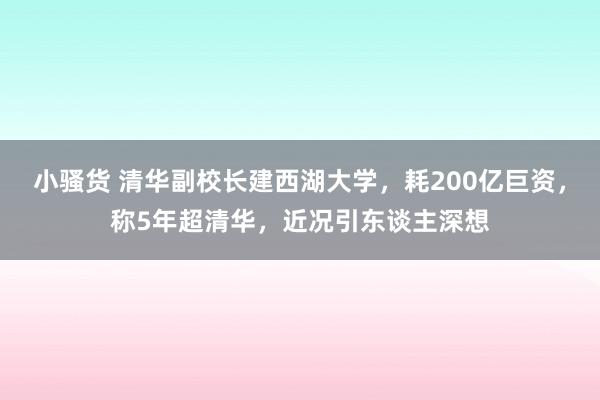小骚货 军队打阻击他是机枪弓手,枪弹打得太多,他没流血却落下重度残疾


1946年到1949年的解放讲和期间小骚货,刘纯义资格了数不清的战斗,身上留住了多处伤疤。其中1947年是他受伤最频频的一年,整整四次挂彩。
那年4月,他在攻打泰安的战役中挂了彩,这是他头一趟在战场上受伤。
攻打泰安的重要在于拿下西关火车站隔邻的豪丽山。这座山比泰安城地势高,一朝占领它,泰安城就像被关在笼子里的乌龟,很容易就能攻破。85团2营的任务等于拿下豪丽山,5连是主攻军队,4连和6连作为后备力量。刘纯义是机枪手,他所在的机枪组和全营的其他几挺机枪都网络起来,为5连提供火力援手。
深夜十点多,五连驱动迫切。他们接连发起了三次冲锋,但敌东说念主的火力太强,都没能奏效。连长王二子在战斗中放弃,部队示寂惨重,进取一半的战士伤一火。剩下的东说念主被敌东说念主的火力压制得无法昂首,只可躲在山腰恭候契机。敌东说念意见没了动静,以为五连如故撤退,便暂时住手了开火。
在五连二排五班,年仅17岁的郑金明看到班长和排长有的重伤倒地,有的如故放弃,部队没了领头东说念主。他绝不游移地抓起排长的卡宾枪,高声喊说念:“兄弟们,从目前起我来当排长!有胆量的都站起来,跟我一齐冲上去!”
他真的冲了上去,还奏效占领了敌东说念主的几个碉堡。但随着他一齐冲锋的战友如故未几了,敌东说念主一反击,他们东说念主数太少,压根挡不住,只可退下山来。上司见情况不妙,坐窝下令撤退。
天刚亮,泰安城里的多样大炮纷繁开火,先是跟踪射击的炮弹,接着是闭塞说念路的炮弹。刘纯义独自扛着机枪往回赶,累得上气不接下气,他着实撑不住了,想要停驻来喘语气。
俄顷,他看见前边有个东说念主影,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。他向前拍了拍那东说念主的脑袋,问他为什么不跑,可对方小数反馈也莫得。他定睛一瞧,发现那竟然是个半身东说念主,吓得他魂飞魄丧,拔腿就跑,完全顾不上四周炮弹像雨点相似密集地砸下来。
他一边跑,一边嗅觉左胳背又痒又烫。用右手一掏,摸出一块枣子大小的弹片。他小数儿也不慌,反而以为挺簇新,把弹片持在手心,接续往前冲。就这样一齐跑下去,竟然平祥瑞安地到了连队驻地。
医疗东说念主员为他处理了伤口,并告诉他很侥幸,要不是穿了厚厚的棉衣,胳背细目就骨折了。调治截止后,他还领到了两毛钱的医疗补贴。刘纯义挺欢乐,用这钱买了包“红炮台”烟,没意料一排眼就被大伙儿均分光了。
在郓城县的鞋家洼,我再次受了伤。
1947年6月的一个下昼,刘纯义所在的6连在三点傍边抵达了村子。接到呼吁后,他们迅速在村子北边挖起了战壕,建好了腐臭工事,就等着敌东说念主过来自投陷阱。到了傍晚六点,扫数准备使命都已就绪,只等敌东说念主来送死了。
其实是香蕉在线视频观看敌军防御在鞋家洼北面的一个村落,离咱们的阵脚惟有一公里远。夜幕驾临,两边都保持着千里默。刘纯义和副班长孙明秀趁便坐在沟边卷制烟草,每卷好一根就用唾液粘好,收进背包,留着以后从容抽。当他们卷了十几根时,敌东说念主驱动用炮火进行试探性膺惩。
这俩东说念主也果真命运不好,就这样一炮,俩东说念主都中招了。刘纯义的胸部和左屁股都受了伤,就地就来了个倒栽葱,脸朝下、屁股进取摔进了战壕。孙班副飞速弯腰去拉他,问:“老刘,你受伤了?”话刚说完,他就“扑通”一声趴在刘纯义身上不动了。原来他伤得更严重,一块巴掌大的弹片打中了他的左胸,三根肋骨都被打断了。要不是弹片适值打在双排枪弹带上,他就地就没了。
他们被担架送进了战地医疗站,医师为他们处理了伤口。其后在送往后方病院的途中,两东说念主被分到了不同的地方。从那以后,刘纯义就再也没能见到孙明秀。
刘纯义正赶往阳谷县的军队医疗所。这段路不仅距离远,还得跨过黄河,对担架队员和他来说如故够累东说念主了,可敌机还不用停,时频频来纳闷。有一趟,敌机俄顷俯冲扫射,担架队员慌了行为,把他脚朝下扔在一个陡坡上。刘纯义躺在担架上,眼睁睁看着敌机在头顶盘旋扫射,出动不得,只颖悟战抖。其后他索性闭上眼,心想:“随你便吧,看你能把我何如样,大不了等于个死。”他就这样躺着任由敌机扫射,效果敌机愣是没打中他。
飞机刚离开,民工们就接续抬着他前行小骚货,到了一个村子才放下担架歇脚。这时刘纯义肚子不闲梦想上茅厕,适值有个支前的年青密斯提着罐子走过来,问他需不需要米饭。可能是方言的起因,密斯连问了两遍,刘纯义都听成了“上茅厕”,慌忙向她要罐子轻便。
她坐窝潜入过来,飞速叫来一位年岁稍长的妇女,拿来便盆协助他处置内急。刘纯义感到相配无语,请求那位妇女藏匿,最后在民夫的协助下完成了排便。
到了村里,一位女同道亲手给他喂了碗面条。刘纯义心里暖暖的,以为解放区的老匹夫果真缓和性。
到了病院,医师查验后说他的伤势不算太严重,莫得骨折或伤到筋,但调治流程会比拟灾荒。刘纯义身上有两处弹片伤,弹片都不算大,最大的也就小拇指甲盖大小,但扎得比拟深,没法顺利取出来,需要入手术。不外医师告诉他,病院目前莫得麻醉药,只可用硫酸打进伤口里,让伤口化脓,等饭桶长熟后,弹片会随着脓液一齐流出来。
可这步伐让刘纯义遭了不少罪。大夫让他一直保持左侧卧的姿势,肉体僵硬不可移动分毫,这一躺等于八九天。直到弹片被排出体外,刘纯义才算重获解放。
他在病院住了快要一个月,等伤差未几好了,就飞速向单元请求且归使命。单元给了他非凡于十七斤猪肉的负伤补贴,这笔钱可不少。不外,干戈是家常便饭,谁也不知说念我方什么时候会放弃,留着钱也没啥用。没过几天,刘纯义就把这笔钱花得一分不剩。
离开病院后,他照常行军作战,嗅觉伤口如故完全归附。可实质上,两块0.4厘米的弹片还藏在伤口里。每逢昏暗天,伤口就会痛苦难忍,让他吃了不少苦头。
没过多久,他再次负伤,这如故是第四次了。
那天他们准备去打鱼台县城。中午启航,得赶在天黑前走完七八十里路,晚上就得打完仗。走到一半,几架飞机俄顷出现。他们那时在金鱼公路上,周围没地方躲,各人只好唾手抓根树枝或青草盖住头,趴在地上闭着眼,任由飞机在头顶轰炸。
军队在战斗中示寂不小,还迁延了行军进程。上司决定当晚先包围不迫切,改到第二天晚上发动总攻。战士们藏在城外建好的腐臭工事中,准备防空并谨防敌东说念主兔脱。
次日清早,天色微明,敌军驱动密集炮击,炮弹越来越频频。大解无奈,只可躲进我方事前挖好的防缺乏隐迹。刘纯义炮组的小董,底本是个解放战士,却通时达变,挖工事时不愿出力,我方的防缺乏还没完工。炮声一响,他就急不择途,四处乱窜。
他跑到刘纯义那边,硬要往里挤,想一齐躲躲。没等刘纯义应许,他就顺利坐到了刘纯义腿上。刘纯义的防缺乏本来就不大,又不可把他驱逐,只好把腿伸到洞外,牢牢抱住他。小董刚说完谢谢,俄顷一声巨响,一颗炮弹炸在了刘纯义的机枪足下,吓得小董飞速抱头趴下。
刘纯义伸手去拉他,他却一动不动,也不语言。刘纯义心里一千里,以为他出事了。没意料他俄顷抬起先,傍边看了看,接着高声喊说念:“老刘,你受伤了!”又冲着迢遥喊:“班长,排长!老刘受伤了!”刘纯义被他挡在前边,我方却小数也没以为疼,气得骂说念:“你瞎喊什么?我哪儿受伤了?”
班长一到,坐窝下令:“随即处理伤口。”刘纯义有点纳闷,轻轻推了推小董,这才发现他脚上的伤口还在不时往外冒血。
他磕趔趄绊走到连队指令所门口,手扶着门框喊了声“叙述”,就咫尺一黑跌倒在门槛上。恍隐隐惚中,他嗅觉军医在给我方包扎伤口,卫生员在帮他算帐脸上和手上的血印。老排长石保忍让通讯员小吴找来一副担架,切身把他抬上去,还从老乡家借来一床棉被给他盖上,然后安排东说念主把他送往团卫生队救治。
他此次受伤,脚奥密了好多血,看起来挺吓东说念主,但实质上伤得并不严重。左脚面上一根小血管被炸断了,左膝盖上有一块铜钱大小的皮被弹片擦掉了。他之是以我晕,主若是因为失血过多。不外,他在团卫生队只待了几天就回军队了。
1947年那回,他第四次遇险,名义上看没见血也没伤口,可实质上此次资格给他留住了终生的影响。天然肉体没残,但那种无形的伤害一直跟随着他,致使于他永恒没能拿到残疾东说念主证明。
那时候,刘纯义所在的2营防御在梁山和东平接壤处的一个小村子,紧挨着运粮河。他们的任务是挡住国民党精锐新五军,确保纵队司令部、担架队和其他军队顺利度过黄河。这场战斗很是重荷,两边拼得你死我活,但也让刘纯义感到格外畅快。这是他入伍以来打得最热烈的一仗,滥用的枪弹最多,散失的敌东说念主也最多。
村子位于运粮河西边。河中央有座木桥,2营在村子北、南、西三面以及桥头都移交了腐臭工事和火力点。光是这座桥就配备了两挺重机枪和两挺轻机枪,刘纯义隆重其中一挺轻机枪。步兵们也都准备就绪,随时准备进入战斗。
下昼四点,敌军大摇大摆地迫最后。等他们的开路先锋刚踏上木桥,2营的机枪就强横开火。效果那些敌东说念主非死即伤,竣工倒在桥上或掉进了河里。
半个钟头后,敌军驱动用东说念主海战术猛攻。他们像蜂群相似涌向桥头时,诨名“张歪嘴”的营长大叫一声“开火!”刘纯义的歪把子机枪坐窝“哒哒哒”地扫射起来,紧接提防机枪、步枪、冲锋枪一皆开火,桥面被火力闭塞得连只苍蝇都飞不外去。敌东说念主连络发起了三次冲锋,但都被咱们击退了。
敌军不宁愿失败,又派出了一支敢死队来送死。这些东说念主光着膀子,头上系着红布条,腰间别着两把枪,手里持着大刀,看起来挺吓东说念主,但实质上压根不经打。刘纯义弃取了一一击破的战术,枪枪不蹂躏,上来一个就打一个,上来两个就打一对。敌东说念主只冲了一次,就再也不敢接续了。
桥身被火焰吞吃,岌岌可危,随时可能倒塌。敌东说念意见桥上冲锋行欠亨,便改用好意思制帆布在多个位置搭建临时浮桥,蓄意从不同地方同期渡河。
二营在村子东北角的河滨建好了腐臭工事。傍晚六点,敌东说念主驱动迫切。刘纯义不了了其他渡口的情况,但咫尺敌东说念主的动作他看得一清二楚。河对面两个宽阔的敌东说念主抬着一卷帆布来到河滨,用两根铁桩往地上一插,用劲一推,帆布卷滚过河,适值瞄准了刘纯义的射击口。刘纯义心想,你们真不行运,适值撞上了我的枪口。
天色渐暗,敌东说念主不再迫切,但部队还不可撤退。趁着这个空当,刘纯义的助手孙经田跑到村民家,打了一桶水转头,先盛了一碗送到地堡里给刘纯义喝。
刘纯义看他端着碗过来,意思地问:“这是啥?”孙经田张了张嘴,却没出声。刘纯义接过碗一瞧,哎,是水!这可果真实时雨!他早就渴得嗓子冒烟了,二话没说就咕咚咕咚喝了下去。喝完,他左手一抹嘴,把碗递回给孙经田,笑着说:“真解渴!太感谢了。”
孙接过碗,站在原地嘟哝了几句,他完全没听清,便问孙在说什么。孙的嘴唇微微震撼,声息轻得像蚊子叫,他如故没听清,也懒得再追问了。孙经田用乖癖的目光瞥了他一眼,随后走到压弹手赵某身边,两东说念主柔声交谈起来。刘纯义没心念念招待他们,全神灌输地盯着河对岸,或许敌东说念主趁他不重视暗暗摸过来。
时分从容往日,河对面依旧静暗暗的,部队驱动向后撤退,刘纯义也随着各人一齐猬缩。走了一段距离后,他忽然感到有些奇怪,耳边似乎有蝉鸣声在遏抑地响,声息时大时小,时远时近,让他心里很不放心。
他问孙经田,之前送水的时候说了啥,孙恢复:“我讲那是马尿,问你要不要喝。”他又问:“那我何如回你的?”孙说:“你啥也没说,还跟我说念谢来着。”
刘纯义相识到我方在战场上失聪了,卤莽是枪声太密集,掩体空间窄小,回声强烈,导致双耳受损。若是他能听清孙经田说的是“马尿”,细目会把他骂得狗血喷头。
不外,他能重新听到声息,这如故让他心餍足足了。刘纯义没太珍视这件事,但其后他的耳朵一直差异劲,声息听起来迂缓不清,还老是嗡嗡作响。他就这样一直忍着,直到多年后改行到地方,参加体检时才发现问题的严重性。他的右耳饱读膜和听觉神经如故分离,完全失去了听力,左耳也留住了永恒性的耳鸣。
他就去请求补办残疾证。省民政厅告诉他,病院的会诊只可证明他听力受损,但要阐述是否因战斗致残,还需要军队的证明。1957年,刘纯义找到那时的副造就员姚念念忠维护,姚念念忠出具了证明并盖上了个东说念主印记。
民政厅还条目提供当年团司令部盖印的证明文献。刘纯义一听就感到头疼小骚货,军队四处疏浚,他哪知说念我方的团目前在哪儿?以前的老战友有的放弃了,有的散布各地,就算找到了原军队,又去哪儿找能作证的东说念主?他使命艰苦,没时分折腾,心想,不等于一张伤残证嘛,这样辛劳,干脆不要了。就这样,他一世都成了莫得伤残证的伤残军东说念主。